旁边站着人,手里攥着根东西。半截胳膊长,沉甸甸,暗沉沉的铁条,一头烧得赤红发亮,滋滋冒着烟。另一头裹着厚厚几层粗麻布,布都烤焦了,冒着丝丝缕缕的糊味。
那地方吵得人耳朵嗡嗡响。空气里全是烧红的铁味儿,吸一口烫嗓子。中央杵着个黑疙瘩,像座小山,底下炉火烧得正旺,映得四壁通红。火苗舔着黑疙瘩的底,发出滋滋的怪声。
抡起胳膊把那烧红的一头狠狠砸向黑疙瘩。当!一声巨响,火星子炸开,像下了一阵烫雨。那赤红的一头明显凹下去一块,暗了些许。他喘口气,又把铁条塞回炉火里。火舌贪婪地卷上来,暗沉的铁再次被烧得透亮,红得刺眼。
抽出来又是狠狠一下砸过去。当!火星四溅。这次凹得更深,铁条的红光也暗淡得更快。他像头倔驴,一声不吭,只是重复。塞进炉火,烧红,抽出,猛砸。动作越来越沉,胳膊上的筋肉绷得像石头。汗水刚冒出来就被烤干了,只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灰白的盐渍。每一次敲打,那铁条似乎都短了一分,凝实了一分,但离最终那耀眼的亮银色,还差着老远。炉火映着他紧抿的嘴和拧紧的眉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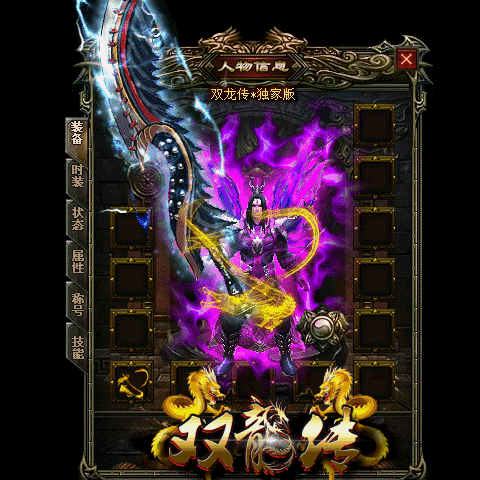
烧红砸下铁条通体只剩一点暗淡的红,砸在疙瘩上,只溅起几点微弱的火星。他喘着粗气,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铁条冷却,显出灰扑扑的本色,表面坑坑洼洼,离那传说中的光华流转,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他盯着这灰扑扑的玩意儿,眼神复杂。炉火还在烧,映着那粗胚,也映着他。火光跳跃,那粗胚沉沉地躺在那儿,离腰带的样子还很远。缺了指甲盖大小一块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