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件袍子挂在最深的角落,墨色仿佛能吞噬光线。流动的暗纹如同活物在呼吸,带着深渊般的不祥。旁人匆匆走过,目光触及便慌忙避开,仿佛多看一秒都会被那纯粹的幽暗灼伤灵魂。它属于传说里那些触摸禁忌的存在。
一个身影却在角落久久伫立。他的手没有犹豫,径直探入那片令人窒息的墨色。袍子落在他肩头的瞬间,袍摆无风自动,暗纹如同苏醒的毒蛇,沿着他的躯体蜿蜒攀附。周遭的空气瞬间冰冷粘稠了几分。
他穿着它踏入狂沙漫卷之地。风沙里潜伏的利爪撕裂空气袭来,带着腥臭。旁人亮起护盾,挥动巨斧。他却只是笨拙地侧身,试图躲避。利爪狠狠划过袍袖,暗纹骤然如墨汁滴入静水般翻涌扩散。没有火星迸射,没有布帛撕裂的脆响,只有一声沉闷如击打湿革的动静。袍袖上留下几道浅浅的白痕,转瞬又被流淌的墨色吞噬殆尽。那利爪的主人反而发出一声困惑的低吼。
更深的阴影之地巨大而沉默的石像守卫被脚步惊醒。它们沉重的石拳裹挟风雷砸落,大地震颤。同伴们灵巧地翻滚闪避,寻找反击的空隙。他穿着那身累赘的长袍,动作迟缓得可笑,眼看就要被石拳碾碎。避无可避,他竟本能地弓起背脊,用那宽大的袍背迎向毁灭性的重击。石拳落下,发出令人牙酸的闷响。巨大的力量让他整个人深深陷进沙土,碎石飞溅。尘埃散开,他咳着血沫挣扎站起,那墨色的袍背却只是剧烈地波动起伏,如同沸腾的泥沼,将石拳的蛮力贪婪地吮吸进去,表面竟无一丝裂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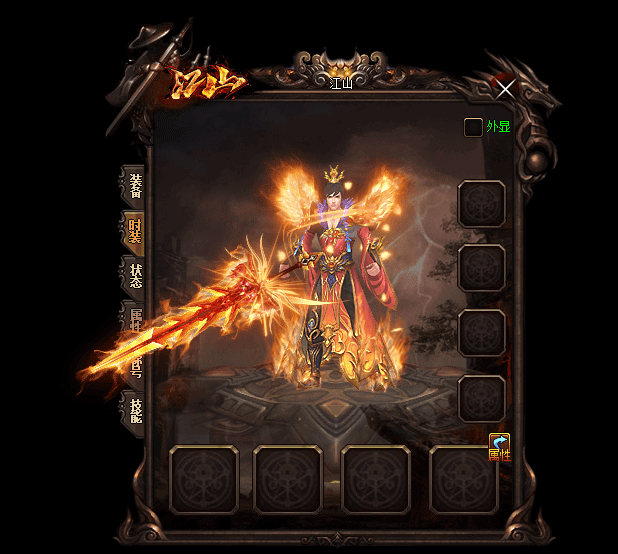
无形的音波如同实质的巨锤,狠狠砸在每个人的精神壁垒上。旁人痛苦地捂住耳朵,光盾明灭不定。他站在那里,笨拙得像块破抹布。尖啸直接轰击在他身上,那墨色长袍骤然膨胀,袍身上所有暗纹疯狂扭动,仿佛无数饥饿的嘴在无声嘶吼。他身体剧烈颤抖,五官因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冲击而扭曲,每一次无形的音波撞击,都让袍子的墨色更加粘稠、更加深邃一分。他成了风暴中一个笨拙却异常坚固的锚点。
混乱平息,他独自站在狼藉之中。墨色长袍依旧沉重地裹着他,暗纹缓缓平复,如同餍足后陷入沉睡的兽。袍子没有给他增添半分凌厉的攻击手段,没有让他变得迅疾如风。它只是沉默地覆盖着他,将他每一次承受的冲击、每一次笨拙的格挡,都化作自身更深邃的幽暗与坚韧。原来最深的防御,并非拒绝伤害。它只是将每一次致命的接触,都贪婪地吞咽下去,以伤为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