暮色染红沙丘时我见过最荒诞的生死局。黄沙里半截断刃还滴着血,穿云箭的啸声里混着此起彼伏的鹤唳,而那个青衫客往嘴里倒的竟不是止血散——翠色流光在琉璃瓶里晃荡,倒像是从瑶池宴上偷来的琼浆。
江湖人总说保命物件该揣在贴胸暗袋,他却把三支琉璃瓶挂在腰际叮当作响。直到被三柄弯刀逼到悬崖那刻,众人才懂这狂徒的算计:仰头饮尽玉髓时,青芒自瞳孔漫向发梢,坠崖前甩出的剑气竟劈开了半座鸣沙山。
黑市里开始流通这种碧色药水,装在雕着蟠螭纹的琉璃樽中。老掌柜眯着眼擦拭柜台,说这玩意喝下去能烧透十二重经脉,代价是三天三夜动弹不得。可总有人揣着烫手的银票来换,仿佛买的不是伤药,而是向阎王赊账的契书。
茶寮说书人拍醒木讲古,说二十年前药王谷焚毁那夜,地火里炼出过七支通体透绿的玉髓。跑堂小二嗤笑着添茶,却见窗边独坐的刀客突然攥紧腰间皮囊,囊中正透出幽幽青光。满堂茶客的呼吸都滞了滞,檐角铜铃无风自动。
疯魔的那场恶战发生在月圆夜。三百黑衣死士围住摘星楼,檐角蹲着的灰袍人却摸出个巴掌大的琉璃盏。当第一滴玉液滑入喉头,他周身爆开的气劲竟将琉璃瓦震成齑粉。后来清扫战场的人说,那些插在青砖缝里的碎琉璃,月光下还在汩汩流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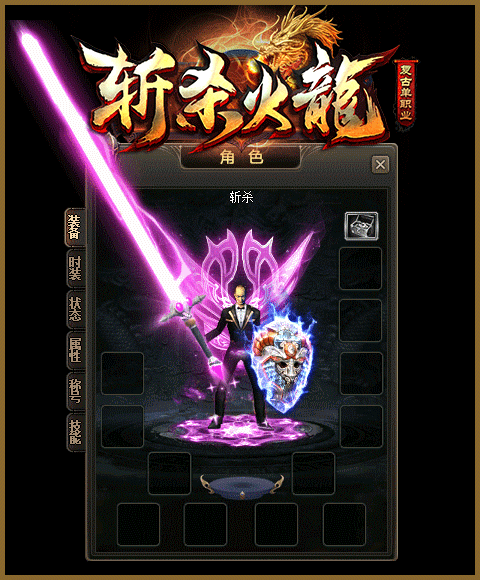
赌坊暗阁常年押着件奇珍:半寸高的玉髓瓶,封着当年某位剑圣临死前逼出的心头血。庄家说这是天下至毒亦是至宝,吞下去能续半炷香巅峰状态。可十年间七任买主都未敢启封,倒让琉璃盏成了最昂贵的镇纸。
